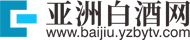
《乖呀乖——为爱狗的你和我》:生命的约定与爱的教育|当前快看
《乖呀乖》万方 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万方与她的乖乖
万方新作《乖呀乖——为爱狗的你和我》(以下简称《乖呀乖》)仿佛是一封长信,写给小狗乖乖,写给岁月,也写给自己。虽然这部长篇非虚构文学作品并未采用书信体格式,但在它涓涓如流的文字背后,在既定的现实与虚广的时空里,有一个接纳作者娓娓细诉与脉脉深情的收件人,那就是“爱狗的你和我”。
从私密到公共
从某种意义来说,《乖呀乖》是单向的,并未预设读者。“爱狗的你”未必是读者“你”,而只是与“我”同类的人。在“爱狗的你和我”之间,作者对乖乖的情感更多回流到自己的记忆密室,她以内燃的方式完成的写作,本质上是内向的、私密的、封闭的。这种“私密”并不涉及隐私,而是独属于创作者个人的极端个体化的经历。除了创作者本人与小狗乖乖,这部书似乎与他人无关。尽管书中也有其他人和狗狗,但它实实在在只是“我”和乖乖的故事。而作为主人公的乖乖因为不具备阅读能力,这部书也不作用于乖乖。作者的创作出发点一如她引用的博尔赫斯的话:“我不为任何人写作,我写作是因为我感到一种这样做的内在需要。”写乖乖,本身就是价值和意义。因此,从根本上说,《乖呀乖》是放下读者的写作,是从作者自身出发,自顾自地记录与倾诉。
 【资料图】
【资料图】
然而,这记录和倾诉太动人,如果作为读者的“你”有幸遇到了这部书,就会进入万方的个人世界,被深深吸引,成为动情的旁观者,并发现这部“私密”作品的公共性价值。因为这部掺杂着个人人生疼痛的作品,是一部生死之书,也是一部情感之书。它是生命过程的见证,是人与动物对等情感的表达,是无垠的虚空中握得住的温暖,是无心插柳中生长出的人间伦理和哲学。它的柔情、平静和深切,是哪怕一切都烟消云散后依然能保持的坚固。因此,这部书不仅仅给“爱狗的”你和我,也给爱或不爱狗、爱或不爱其他的所有读者以爱的教育。所谓意义大于形象,《乖呀乖》就这样从私密走向了公共。
被改变的人生
万方记录的是一场生命的约定。她与乖乖十六年的相依相伴是见证生与面对死的悲欢旅程。乖乖进入作者生活,无疑是一场陪伴式拯救。陪伴的目的是对抗——对抗恐惧,对抗孤独。因为乖乖是作者面临失去爱人的恐惧与无助时到来的,作为新的陪伴,她让作者坦然接受和面对生命过程,学会和死亡相处。在生离死别中,乖乖就是那张接住万方的网。当一个生命消逝,另一个生命以呼吸、体温、眼神显示存在、表达依赖,世界便与孤独中的坠落者有了关系,重新建立了稳定的秩序。生命如此具体,可触、可感、可知,宇宙之大,时空之无涯,未来之不可知,都在这跃动的生命面前改变了形态,化身为扎实、安稳乃至喜悦。因此,万方说:“感谢狗,让我在某些时候化作他们中的一员,每当我变成狗,平安无事。”“孤独,那么凶狠的角色,却在一条小狗面前如此轻易地败下阵,而小狗什么也没干,动都没动,只歪着头朝我望着,就把孤独吓跑了,逃之夭夭。”正是这个小生命,改变了作者的人生。除了陪伴,还带来了生命的放松与解放。
“或许狗狗才是最终的主人,他们拥有改变人的能力。”因为乖乖,作者认识了很多狗和很多人。对她来说,人似乎分成了两类,养狗的人和不养狗的人。她的世界有了新的奇妙。与其他狗主人之间无功利的社交,简单到甚至不需要知道对方的姓名。同样的“铲屎官”身份,同样是爱狗的人,就足够形成默契。尤其珍贵的,是作者通过狗看到了人,看到了人性中的神性。自己不养宠物但收留了流浪狗的B女士,坦然面对生活磨难、毫无悲苦的咖啡妈,一定为球乖乖找个爱她的好人家的小冉……在他们这里,爱、责任、义务同是生命契约的条款,狗和人是平等的,理应获得同样的关注和尊重。传说中美国狗证上的九句话,实在让人柔软,那是狗狗对主人说的话,是一种生死依托与交付。对于狗狗,主人是全部,是上帝一样的存在。他/她是你的,无条件,无保留,不计后果。决定养狗就应当视狗狗如家人,这是从情感到伦理的自然结论。
在乖乖与主人的生活中,表面看起来,是乖乖需要主人,但在特殊的人生情境中,显然主人更需要乖乖。并且,万方发现,所谓需要或被需要,其实可以脱离具体情境,因为“人不仅有物质上的欲望,还有一种高于一切的渴求,那就是被需要,我们需要被需要,我们心甘情愿付出,甚至不觉得是付出,是的,毫不计较”。的确,在需要和被需要之间,“被需要”赋予人超越个人欲求的责任,彰显人的重要性,而承担责任是人性高贵的表现,是人自我实现、自我确认的方式之一。狗狗能够治愈人生荒芜处的“没意思”、无意义,因为被需要本身就是价值和意义。这朴素但易被忽视的人生哲学,在乖乖与主人的相伴中获得了阐释。
“写什么”更重要
写狗,是一个独特的文学选材。中外作家笔下都不乏狗的形象,西方文学又似乎更钟情于狗的书写。玛格丽特·桑德斯的《一只狗的自白》、尤金·奥尼尔的《一只狗的遗嘱》、弗吉尼亚·伍尔芙的《阿弗小传》、石黑谦吾的《再见了,可鲁》等作品,都能看到文学创作者对人与动物情感的关注。不过,这些作品多属虚构类,虽有真实生活基础,但与非虚构的《乖呀乖》还存在创作定位与阅读感受上的差异。从文体选择上,或许只有美国作家雅比凯尔·汤玛斯的自传性作品《三狗生活》可与《乖呀乖》并论,但其书写对象是三条狗,且是不同的经历、不同的感受。
中国很多文学名家也都写过狗。老舍、梁实秋都写过题为《狗》的短篇散文,但狗与他们的个人生活并未发生深切的情感关系,他们的写作目的都在于借狗刺世;杨绛《干校六记》之一《小趋记事》和巴金的《小狗包弟》足够感人,有可爱的小狗形象,也有作家个体情感投入,但也是短章。采用长篇纪实文体来写狗,《乖呀乖》在中国文学创作中当属首例。万方在《乖呀乖》中引用著名漫画作者斯科特·亚当斯的话:“写作技术成熟的人最关心的不是怎么写,而是写什么。灵感更依赖身体,而不是大脑。”的确,当技术成熟的作家不再为“怎么写”困扰时,代表眼光、态度、立场的“写什么”便成了第一要务。
《乖呀乖》写的是什么?是真情,是深情,是柔情。万方以家人般深挚的情感,写出了一条乖巧、机灵、纯净、敏感的小狗乖乖的形象,写出了人类情感的热度、浓度、烈度。无论你是不是爱狗的人,都无法不被感动。(作者为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原教授)
流程编辑:u060
标签: